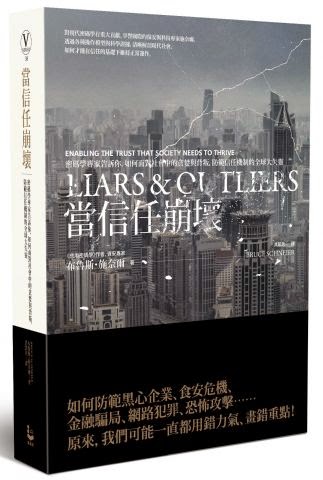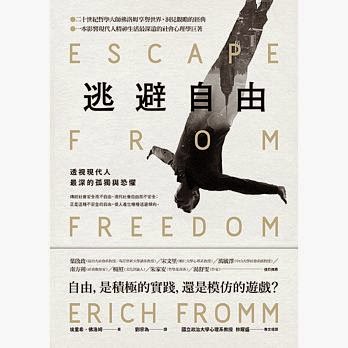《二十一世紀資本論》第二部分從宏觀角度討論了所得不平等的歷史。我們瞭解到,從資本/所得比來看,十九世紀末西方國家的財富規模相當於五至六年的國民所得,到二十世紀上半葉大幅度下降,回落到相當於二至三年國民所得的水準。
但在過去半個世紀,財富規模再度膨脹,二十一世紀的財富規模很可能會回到甚至超過十九世紀末的水準。從資本所得占國民所得的歷史演變來看,儘管趨勢相對和緩,但大體上也呈現出一條U形曲線。其基本結論是,二十一世紀將重蹈十九世紀的覆轍。
皮凱提的宏觀指標很雄辯、直觀,但從個人層面來說,我們很難感受到其意義何在。資本規模相當於三年的國民所得,還是相當於七年的國民所得,跟我們的日常生活有什麼聯繫呢?
在接下來的幾章中,皮凱提將從微觀的角度,討論所得不平等對我們每個人的影響。我們將瞭解到,所得不平等有各種各樣的形式,其背後有各種各樣的機制,有些不平等未必是壞事,但有些不平等將葬送社會進步。我們也將了解到,在所得不平等的社會臺階上,我們大約處於哪個水準,在我們之上和在我們之下的都是什麼人。最後,我們會進一步深思,這些不平等都是怎麼來的,未來的社會會不會變得更加不平等。
拉斯蒂涅的艱難選擇
在巴爾扎克的小說《高老頭》裡,拉斯蒂涅是一個野心勃勃但不通世務的外省大學生。他一心想出人頭地,想當一個法官。心狠手辣的沃德林跟他說,這條路根本就走不通。大學畢業最多到一個小地方當代理檢察,年俸一千法郎薪水,到三十歲時會漲到一千二百法郎。混得好,有靠山,到四十歲可以競爭首席檢察官。但是全法國只有二十個首席檢察官的空缺,而候補的有兩萬人。或者,拉斯蒂涅也可以選擇當律師,但這條路更辛苦。
沃德林說,你數數看,五十歲左右每年掙五萬法郎以上的律師,巴黎有沒有五個?他開導拉斯蒂涅:「雄才大略是少有的,遍地風行的是腐化墮落……在這個人堆兒裡,不像炮彈一般轟進去,就得像瘟疫一般鑽進去。」他建議拉斯蒂涅去追求一位貴族小姐,而他則去派人謀殺這位貴族小姐的哥哥,這樣拉斯蒂涅就可以到手一百萬法郎的陪嫁,而他索要二十萬法郎作為報酬。
皮凱提在書中講到這個故事,不僅是要說明十九世紀曾經出現過極度的財富不平等,而且是要提醒我們,財富不平等會帶來巨大的社會影響。年輕一代將會面臨和拉斯蒂涅一樣的艱難選擇:是努力工作,靠自己的拼搏出人頭地,還是靠「靠爸」、「幹得好」,或是「嫁得好」?
十九世紀,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說在十九世紀之前,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一個人要想進入上流社會,唯一的希望就是通過繼承或婚姻。看看珍‧奧斯汀小說中的主人公,除了談戀愛什麼也不幹。美國相對平等一些,西部小說宣揚的是自我奮鬥的樂觀精神,但別忘了,在美國的南方照樣是靠繼承遺產。看看小說《飄》(Gone with the Wind)裡面的上流社會,哪個不是靠蔭祖宗的德?
二十世紀以來,財富不平等程度有了急劇的下降,遺產繼承的重要性不如往昔了,相信自己的努力,靠個人奮鬥出人頭地,成了新的社會風氣,這幾乎是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總體來說,這種樂觀積極的風氣一直延續到了現在,但是,看看未來,我們還能如此自信嗎?事實上,從二十世紀後半葉起,全球範圍內的不平等程度已經在加劇,但在經濟高速增長的時候,人們的忍耐程度或許會更高,他們對未來會寄予更樂觀的期望。全球金融危機之後,隨著增長的潮水退去,人們對不平等現狀的抱怨會越來越多。借用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二○一一年在《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上發表的一篇文章,我們已經進入「全球憤怒」(global indignation)的時代。
不要再像鴕鳥一樣把頭埋在沙子裡面,假裝什麼都不知道、什麼都沒有發生,聽任年輕的拉斯蒂涅們自己做出痛苦的選擇。如果他們真的做出了選擇,我們就該後悔了。
兩種不平等
簡言之,所得不平等有兩種形式,一種是勞務所得的分配不均,一種是資本所得的不平等。之所以要做這樣的區分,是因為兩種不平等的程度、背後的機制,以及其對社會的影響都是不一樣的。
勞務所得的分配不均程度明顯低於資本所得的不平等。真正令人觸目驚心的是資本所得的不平等,連資本所得相對來說最平等的社會其不平等的程度都要甚於勞務所得最不平等的社會。但並非所有的不平等都是不好的,以勞務所得的分配不均而言,導致勞動者所得不同的因素中,有些是正常的,甚至是積極的。
比如,勤奮的工人理應比懶惰的工人所得更高,聰明人理應比笨人賺得更多,一般來講人們也不會有異議。就勞務所得的分配不均而言,也可能會有不合理的因素。
每個人的天賦和技能不同,但這個社會對不同天賦、技能的市場需求卻是不一樣的。同樣是體育選手,拿了奧運會金牌的體操運動員、舉重運動員,最後可能淪落到去澡堂給別人搓背,而屢戰屢敗的中國足球隊,為什麼踢得那麼臭,卻賺得那麼多?教育對勞務所得不平等也有很大影響。有一個故事說,一個北京建築工程師和湖南農民工聊天,兩個人同一年高考,湖南農民工的考分遠遠比北京建築師的分數高,卻落榜了,可十年之後,一個成了農民工,一個成了白領,這公平嗎?
很多政策和制度因素也會影響到勞務所得的不平等程度。比如,是否允許工人組織工會與資本家談判?這將影響勞方和資方相對的討價還價能力。比如,是否要限制企業高級主管的所得?如果不加以限制,完全可能出現天價年薪,因為企業高層在很大程度上能夠左右企業的薪酬委員會。另外,安隆和雷曼兄弟的高層應該拿那麼多的獎金嗎?
影響資本所得不平等的因素中,也有合理的部分。比如,我們預見到未來可能會有所得或支出的不確定性,就會增加儲蓄,這叫作「預防性儲蓄」,這是一種明智而審慎的行為。《伊索寓言》中寫道,螞蟻在夏天的時候忙著儲存過冬的食物,知了卻天天唱歌嬉戲,到了冬天只好餓肚子。再比如,著名經濟學家弗蘭科‧莫迪利安尼(Franco Modigliani)曾經提出過「生命週期理論」,意思是說在人的一生中,不同的時期會有不同的儲蓄行為。一個人少年時期靠父母養活,是負儲蓄;中年時期要養活一家老小,還要為自己的晚年考慮,儲蓄自然會增加;到了退休之後,就會把過去的儲蓄逐漸用掉,又成了負儲蓄。不過,這些因素都不是決定資本所得不平等程度如此之深的最重要原因。
一個社會的所得不平等程度到什麼水準會出現矛盾和衝突呢?當一個社會所得最高的一○%人口拿走了一半以上的總所得時,警鐘就已經敲響了。法國大革命前夕,所得最高的一○%階層得到的所得很可能占總所得的五○%,甚至是六○%以上。
設想一個社會所得最高的一○%群體把全社會所得的九○%都盡收囊中,這個社會一定要通過高壓政策,才可能壓制人們的不滿和反抗,但革命終歸是會爆發的。
所得不平等之所以重要,不是因為其本身重要,而是我們能否證明所得不平等的合理性。如果一個社會的公民認為所得不平等是合理的、可以接受的,那麼可能引發社會矛盾的不平等程度的閾值也就更大;但如果無法說服大家,富人的錢來得光明正大,導致社會矛盾的不平等程度的閾值就會偏小。
皮凱提談到,在兩種情況下,一個社會將出現極端的所得不平等,一種是「收租者社會」,另一種是「超級經理人社會」。
在前一種情況下,所得不平等的主要來源是資本所得的不平等。財富分配極其不公,而一個人能有多少所得,更多地不是靠其勞務所得,而是靠資本所得,這些資本又主要是從上一代繼承下來的。這一種情況的代表就是大革命前夕的法國,所得最高的一○%群體佔有了九○%的財富,而所得最高的一%群體佔有了五○%的財富。在後一種情況下,所得不平等的主要來源是勞務所得的分配不均。
這是一種「贏家通吃」的社會。如果你是體育明星、大牌演員、有名的企業家,你拿到的所得會遠遠高於其他人。表面上看起來,這一切都是合理而正常的,但其實不然。我們姑且不論,老虎‧伍茲或安潔莉娜‧裘莉的高所得中,有多少是靠個人的天賦和努力、有多少是靠運氣,只論雷曼兄弟、AIG(美國國際集團)、房利美和房地美的高級主管,再往前算到華爾街醜聞時期出了事的安隆、世通,它們的高層拿那麼高的薪酬,甚至是靠納稅人的錢得到救助之後繼續拿那麼高的獎金,難道是合理的嗎?這種「超級經理人社會」的不平等更具有欺騙性,很多人認為這是市場經濟的結果,其實這是一種市場失敗的表現。
未來會出現什麼情況呢?遺憾的是,以後最可能出現的情況是,「收租者社會」再度回歸,而「超級經理人社會」依然故我。這兩種可能導致所得不平等的現象將同時發生,甚至互相推動。我們將步入一個日趨不平等的極端年代。
以上摘自《三小時完全吸收,看懂21世紀資本論》